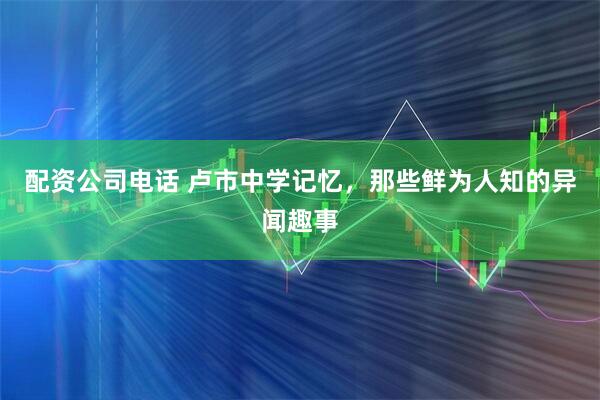
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卢市中学度过的。1980年代初,我们习惯称卢市中学为“十三箍中学”。那是一段交织着欢笑与汗水、满含故事与温情的时光,每一个片段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有些奇闻趣事让人印象深刻。
沈老师的“钟声”,让校园充满了生机与希望。
每天,校园里最早奏响的旋律,是沈光祖老师的“钟声”。彼时学校尚无电铃,沈老师便主动承担起打铃的职责。他既要教学,又要负责“打铃”工作。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落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,他那清瘦而坚定的身影便准时出现在挂大钟的地方。他手握钟槌,神情专注而庄重,用力一挥,清脆的钟声便在寂静的校园里回荡开来,仿佛是大自然与校园生活的和谐共鸣。
这钟声,如同温暖的召唤,唤醒了还在沉睡中的我们,引领我们开启新一天的学习征程。课间休息、上下课,他的钟声分秒不差,宛如精准的时钟,将一天的学习生活编排得有条不紊。我常常望着他打铃时的模样,那专注的神情、有力的动作,仿佛时间都为他而静止。这钟声,不仅仅是作息的提示,也是卢市中学独特的文化符号,更是像穿越岁月的长河,承载着我们对校园生活的最初记忆。
展开剩余83%学校里“半边户”老师,撑起学校教学“一片天”。
在卢市中学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一“半边户”老师。这些老师可能占了当时卢市中学老师总数的80%。他们的配偶大多是农民,住在乡村里从事农业生产,收入微薄,家里生活的重担压在这些“半边户”老师们的双肩上,但他们从未有过丝毫的抱怨。平时,他们在学校里兢兢业业地上课,用渊博的知识和耐心的教导,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。“拿起教鞭当老师,放下教鞭当农民”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。每到周末,他们就会骑着那破旧的自行车,驮着一些生活用品,匆匆往家赶。
记得有位李老师,他的自行车链条总是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,仿佛在诉说着他生活的艰辛。但他从不觉得苦,因为他知道,家里还有等着他照顾的家人。周一回来时,他虽然满脸疲惫,但一走进教室,就立刻精神抖擞起来。他站在讲台上,用那充满激情的声音为我们讲解着每一个知识点,仿佛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他们这种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努力平衡的精神,如同一座座巍峨的高山,让我们心生敬意。可是就是这些“半边户” 老师们支撑了卢市中学的教学工作,也带领卢市中学学子们在那个时代的高考中创造了许多佳绩。
男女同学的“关系”,让彼此成为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在那个略显保守的年代,卢市中学里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有着一种无形的界限,大家忌会“私下接触”,担心流言蜚语。即便彼此在同一个班级学习了很久,却永远像是熟悉的陌生人。课间休息时,男同学聚在教室的一角高谈阔论着球赛、武侠小说;而女同学则在另一处轻声细语地分享着少女心事。在校园的小径上,男女同学相遇,也只是匆匆一瞥,便各自低头走开,仿佛多说一句话都会引起旁人异样的目光。
这种微妙的氛围,让青春期的懵懂情感只能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,成为了我们心底难以言说的秘密。即使男女同学之间有点“两情相悦”的感觉,但也不敢表露出来,或者大胆地去追求。一方面那个年代学校反对谈恋爱,另一方面男女同学担心谈恋爱分心走神,影响学习。虽然那时候,女同学还是愿意与我打交道,但碍于学习的压力,也没有心思去深入交流了解。现在回忆起来,我能记起来的女同学寥寥无几。
班级之间的“冲突”,成为平静的校园生活中“小插曲”。
有一天下晚自习后,一个理科班的男同学不知为何突然挑衅了隔壁文科班的几位女同学。那位男同学平日里就有些调皮捣蛋,仗着自己身高体壮,便对女同学进行言语上的侮辱。女同学又羞又恼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跑回教室。这一幕被文科班的一位男同学碰了个正着。这位男同学给班里的几位男同学说了此事,他们义愤填膺,觉得不能让自己班的女同学受这样的欺负。于是,这几个男同学就冲进理科班找那位男同学论理,没想到双方情绪失控,文科班男同学打了那个男同学。理科班那位男同学拿着板凳角,追打文科班男同学。文科班男同学迅速跑出理科班教室,消失在校园黑夜里。那时灯光不好,“冲突”发生很快,又迅速结束。
第二天早上,学校调查这个事情,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,也不知道谁参与了这次“冲突”。最后,两个班的班主任在课堂上借这个事教育了一下大家,最终不了了之。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,同学之间应该相互尊重、友好相处,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伤害到别人。
胡家老头的“厨房”,是我们吃饭时最向往地方。
作为教师子弟中的一员,我可以沾我父亲吴贤成老师的光,在教师食堂吃点好菜,但好菜的价格特别贵。我舍不得吃,每次只打最便宜5分钱一份的红烧粉条。说是红烧粉条,但没有肉,全是用猪油渣烧成,油水比较重,正好满足缺油水的我。学校的教师食堂,是我吃饭时间最向往的地方,而这里的灵魂人物,当属胡家老头。他是教师食堂掌勺的大厨,那精湛的厨艺堪称一绝。每当他系着围裙,在炉灶前忙碌时,整个食堂都仿佛弥漫着幸福的味道。他做的肉炒豆干,豆干吸满了肉的鲜香,口感劲道有嚼劲;粉蒸肉,肉质鲜嫩多汁,米粉软糯香甜,入口即化;红烧粉条,粉条Q弹爽滑,汤汁浓郁醇厚,让人回味无穷;瘦肉炒榨菜,味道相当地道。
每次开饭的铃声响起,我们就像一群欢快的小鸟,迫不及待地冲向老师食堂。胡家老头总是笑容满面地站在窗口,一边熟练地给我们打饭,一边用那和蔼的目光看着我们。他似乎能读懂每个同学的心思,总会偷偷给那些学校书记、校长的小孩多盛上一点肉,把最精华部分打给他们。当时年少无知的我,看不懂其中的名堂,只是感觉他们运气好,正好遇到了肉多部分。现在回想起来,觉得好笑,其实学校也是一个小江湖。
高考前的“预考”,让许多人大学梦想化为了“泡影”。
那时候的高考竞争异常激烈,录取率非常低。通常,正式高考前的三个月,天门县要组织一次全县预考。这次预考就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许多同学面前。大约一半的同学会在预考中因达不到预考分数线惨遭淘汰,无缘参加人生大考一一高考。为了能通过这场残酷的战役,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。
清晨,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,我们就已经坐在教室里,借着微弱的晨光背诵英语单词和语文课文。课间休息时,教室里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,取而代之的是同学们热烈讨论题目的声音。夜晚,当整个校园都沉浸在寂静之中,我们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,微弱的灯光照亮了我们求知的眼眸。周未节日,仍有许多同学不回家,留在学校里加班加点学习。预考的压力如同沉重的枷锁,但我们从未想过放弃。因为我们知道,只有通过这场考验,我们才能离自己的大学梦想更近一步。但许多同学还是倒在了预考这个关口。预考淘汰后,许多同学放弃了学业,从而走上了另外的人生方向。我与许多同学自预考后,就没有再见过面。
学校年终分肉分鱼,是那个年代学校的“教师福利”。
为了改善老师们的生活,学校别出心裁地搞起了副业,养猪养鱼。学校食堂前面的小池塘,碧波荡漾,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;旁边的猪圈里,小猪们哼哼唧唧地叫着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每到过春节前夕,学校就会把养的猪杀了,把养的鱼捞起,给老师们发福利。当老师们领到猪肉和鱼时,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,更是学校对老师们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尊重。老师们带着这些福利回家,与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,那一刻,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浓浓的年味。
如今,我已离开了卢市中学40多年了,卢市中学也早已不存在,那些“半边户”老师中许多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,但那些在卢市中学的日子,却成为了我人生中宝贵的经历。那些有趣的老师、难忘的同学,奋斗的岁月,美好的校园时光,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温暖回忆。
吴为为,湖北天门市净潭乡白湖口村人。1984年考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,英语专业八级。1994年赴中印边境边防部队代理连长。2002年赴联合国驻刚果(金)特派团担任军事观察员。曾在原成都军区机关、成都市政府办公厅担任多个领导职务,多次立功授奖。担任过《成都商报》特约评论员,《华西都市报》特约撰稿人配资公司电话,《成都政报》编辑部主任,先后发表过军事小说、军事论文和军事理论文章100多篇。
发布于:湖北省辉煌优配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